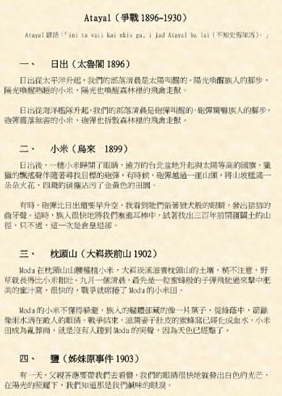〈Atayal(爭戰1896~1930)〉
Atayal(爭戰1896~1930)
Atayal諺語:「ini ta vaii kai nkis ga, i jad Atayal ba lai(不知史焉知活)。」
一、日出(太魯閣1896)
日出從太平洋升起,我們的部落清晨是太陽叫醒的。陽光喚醒族人的腳步,陽光喚醒熟睡的小米,陽光也喚醒森林裡的飛禽走獸。
日出從海洋艦隊升起,我們的部落清晨是砲彈叫醒的。砲彈驚嚇族人的腳步,砲彈震落無害的小米,砲彈也拆散森林裡的飛禽走獸。
二、小米(烏來1899)
日出後,一穗小米睜開了眼睛,遠方的台北盆地升起與太陽等高的國旗,獵獵的飄搖聲伴隨著尋找目標的砲彈,有時候,砲彈越過一座山頭,將山坡種滿一朵朵火花,四濺的硝塵沾污了金黃色的田園。
有時,砲彈比日出還要早升空,我看到牠們張著狼犬般的眼睛,發出狺狺的齒牙聲。這時,族人很快地將我們塞進耳棒中,試著找出三百年前開疆闢土的山徑,只不過,這一次是倉皇退卻。
三、枕頭山(大嵙崁前山1902)
Modu在枕頭山山腰種植小米,大嵙崁溪滋養枕頭山的土壤,稍不注意,野草就長得比小米粗壯。九月一個清晨,最先是一粒蜜蜂般的子彈飛馳過來擊中肥美的蜜汁窩,很快的,戰爭就席捲了Modu的小米田。
Modu的小米不懂得躲避,族人的軀體卻藏的像一片葉子,從綠蔭中,箭鏃像雨水洒在敵人的眼睛。戰爭結束,滋潤妻子肚皮的蜜蜂窩已經化成血水,小米田成為亂葬崗,就是沒有人聽到Modu的哭聲,因為天色已經黯了。
四、鹽(姊妹原事件1903)
有一天,父親答應要帶我們去看鹽,我們的眼睛很快地就發出白色的光芒,在陽光的照耀下,我們知道那是我們鹹味的眼淚。
有一天,我們啟程到濁水溪畔的姊妹原,布農族干卓萬社族人攜帶物品與酒,後面有些東西閃閃發亮,我以為我知道那是白色的鹽粒。
有一天,父親和族人一百三十多人醉臥姊妹原,閃閃發亮的刀刃收割頭顱,那一年,黑色的濁水溪發出紅色的光芒,流動的溪水都不肯回來。
有一天,我翻閱「理蕃誌稿」,從泛黃的頁面找到一顆晶瑩剔透的鹽,後來他們都撲到我的臉龐,讓我再一次看到流著淚水的雅爸和一百多位族人。
五、槍(芃芃山1910)
一支槍走失了一顆鉛彈,走失鉛彈的槍再也追不回森林裡的野獸,森林裡的野獸不再滋潤孩童的皮膚,悲傷的槍只能等待生銹。
一百支槍走失了槍管,走失槍管的槍枝再也追不回部落裡男人的榮耀,部落的男人不再安慰女人的肚皮,哀傷的槍只好等待老死。
一千支槍走失了火藥,走失火藥的槍枝再也追不回芃芃山的神話,芃芃山的神話不再傳述莫那波族人的耳朵,寂寞的槍只好等待哭泣。
六、江山如畫(北勢群1912)
祖靈祭過後的冬日,日人在大克山設置了巨大的畫板,黑色的彩筆沾滿紅色的顏彩,我看到他們在我們的部落恣意的揮灑。祖靈祭過後的冬日,整個天空瀰漫著燦爛的光澤,遠方的大霸尖山升起七彩的彩虹橋。
祖靈祭過後的冬日,日人為戰死的警部補神谷伊三郎默默哭泣。在月亮的掩映下,畫布上雅爸的頭顱在左上角,族人的腿是原野的草,軀體是堆疊的石塊,像極了被撕裂的繪畫,我看到族人微笑地走上彩虹橋。
七、石碑(李棟山1913)
李棟山上站著砲彈般圓柱體的石碑,石碑上站著總督佐久間左馬太,總督衣襟上的徽章照耀著奇那基、馬里闊丸和合歡群族人的天空,整個天空因此詭譎地笑了起來。
有一天石碑走下李棟山,經過炮火焚燬的部落、經過棄擲織布機的河流、經過尋找乳房的嬰孩身邊,最後來到荒蕪的空地擦拭身上的黥面,直到石碑成為大地的孩子。
八、箭(太魯閣1914)
敵方的部隊從立霧溪前進,敵人像暴漲的河水淹沒田園。沒有人看見一支無形的箭緩緩前進。
敵方的部隊從合歡山前進,敵人像秋天的落葉掩蓋穀倉。沒有人看見一支無色的箭緩緩前進。
敵方的部隊從巴托蘭前進,敵人像夏天的流火灼傷族人。沒有人看見一支無味的箭緩緩前進。
當敵人的統帥來到太魯閣斷崖巡視,一支歷史的箭,剛剛完成進出總督那一雙甜蜜小腿的任務。
九、影武者(馬里闊丸、金那基仇殺事件1919~1926)
我們都知道仇殺始於塔克金社副頭目誤將烏來社族人視為猴子而射殺之。
烏來社族人糾集馬里闊丸群像一條河流流過塔克金溪。塔克金社族人糾集金那基群像一條流火吞噬馬里闊丸溪。後來我們都知道「水火不容」的故事了。
只有日警最照顧這兩個社群,連續七次落葉的時間,馬里闊丸與金那基分別秘密收到了槍枝與彈藥,他們都說日警是我族的恩人,直到饑荒阻止了仇殺。
十、算數問題(霧社事件1930)
日人搭救一個荷歌社的孩童,日人用心的教導孩童算數,一顆頭十顆頭百顆頭,孩童一邊數一邊默念族人的名字:瓦歷斯‧‧‧‧‧‧莫那‧‧‧‧‧‧比浩‧‧‧‧‧‧尤帕斯‧‧‧‧‧‧蘇彥‧‧‧‧‧‧直到天也昏、地也黯了。
日人搭救一個荷歌社的孩童,日人用心的教導孩童算數,日本加上荷歌社等於服從,日本加上十座部落等於效忠,日本加上百座部落等於效命,直到我們的孩子成為天皇的子民,直到我們的孩子都成為南進的軍伕。
(p.1990s)
瓦歷斯‧諾幹授權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