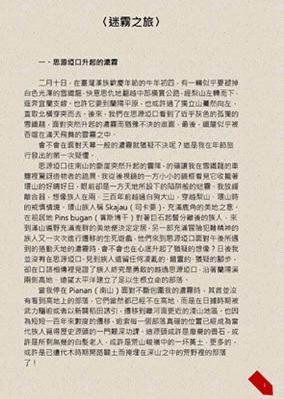〈迷霧之旅〉
一、思源埡口升起的濃霧
二月十日,在臺灣漢族歡慶年節的牛年初四,有一輛似乎要褪掉白色光澤的雪鐵龍,快意思仇地翻越中部橫貫公路,經梨山左轉而下,逕奔宜蘭支線。也許它要到蘭陽平原,也或許過了獨立山驀然向左,直取北橫穿突而去。後來,我們在思源埡口看到了近乎灰色的孤獨的雪鐵龍,面對突然升起的濃霧而猶豫不決的畫面,最後,鐵龍似乎被吞噬在滿天飛舞的雲霧之中。
會不會在面對天幕一般的濃霧就猶疑不決呢?這是我在年節旅行發出的第一次疑懼。
思源埡口往南山的斷崖突然升起的霧陣,的確讓我在雪鐵龍的車體裡驚訝造物者的詭異。我從後視鏡的一方小小的鏡框看見它收攏著環山的好晴好日,眼前卻是一方天地所設下的陷阱般的迷霧。我放緩離合器,想像族人在兩、三百年前越過白狗大山,穿越梨山、環山時的戒慎情境。環山族人稱Skajau(司卡要),充滿鹿角的美地之意。在祖居地Pins bugan(賓斯博干)對著巨石起誓分離後的族人,來到滿山遍野充滿鹿群的美地便決定定居,另一部充滿冒險犯難精神的族人又一次次進行遷移的生死遊戲,他們來到思源埡口面對午後所遇到的捲動天地的濃霧時,會不會也在心底升起了猶疑的想像?日後我並沒有在思源埡口,見到族人遺留任何凌亂的、錯置的、猶疑的腳步,卻在口語相傳裡見證了族人終究是勇敢的越過思源埡口,沿著蘭陽溪兩側高地、遠望太平洋建立了足以生根立命的部落。
當我停在Pianan(南山)面對不斷包圍我的濃霧時,其實並沒有看到高地上的部落,它們當然都已經不在高地,而是在日據時期被武力驅迫或者以新闢稻田誘引,遷移到離河面更近的淺山地區。也因為短短一百年來數度的遷移,追索每一個部落真確的位置已經成為當代族人覓得歷史源頭的一門艱深功課。這源頭或許是廢棄的疊石,或許是所剩無幾的白髮老人,或許是荒山峻嶺中的一坏黃土,更多的,或許是已遭代木時期開路闢土而掩埋在深山之中的荒野裡的部落了!
隨著宜蘭支線緩緩下降,南山以下,蘭陽溪以開闊的河面迎接一位疲倦的旅人歸來,我在宜蘭西面的山腰下俯瞰疾駛而過的車陣時,並無從確知旅人所為何來?也許就只是一次短暫的旅行吧!
也許又不是!
二、「中平 保」在大濁水社嗎?
旅行的本身或終究僅只是一團錯綜複雜的迷霧。
沒有鐘聲的夜半在異地醒來,窗外黑幕隱藏著耐人尋味的雨聲,桌上散亂地錯置一張張資料與地圖,資料是從日據時期理蕃雜誌上翻譯過來的一堆已然陌生的人名、地名。在那個時代,我們的族人通常擁有兩個名字,一個是族名、另一個是代表皇民化標記的日名,目睹著井上、原、山川、志良、高井的名字時,我們幾乎無法辨析那是什麼樣的一張面目,在夜色掩盡的斗室中,它們宛如一層層自思源埡口升起的巨霧。這一些我們所知道的日名,在國府之後又改換了另一個陌生的名字──漢名,下一個世代,人會不會又領著一個全然不相關的名字呢?黑幕以巨大的暗啞回答;相同的是,我們的族名似乎就安安靜靜隱匿在歷史的黑幕之中,像隻冬眠的獸。
上午按照行程尋找冬眠的獸。
蘇澳以南,千萬年的太平洋與山崖握手廝磨,蜿蜒的蘇花公路宛如曲捲山壁的蛇族。一路行到資料上的大濁水社時,蛇族為溪流所阻,牠跨一個身,蛇背成為新建的水泥橋面,向南又再次暢快淋漓地吐著蛇信而行,右側是如今我們所稱呼的「澳花」。它最早的地名其實是莫瑤社(Moujau),族人來到此地遊獵時發現了許多「紅葉樹」,族人日後稱此地為Degalan,到今天,Degalan的舊地名已經無法從孩子的嘴巴裡吐出來了。澳花下部落的學童愉快地回答著:這裡是澳──花──村──不是什麼「打卡蘭」。我懷疑澳花村的「花」或許是「紅樹葉」的紅吧!但沒人證實這一點。
我來到村中,年輕的族人果然不認得「中平 保」,風從他的腦後吹過,幾抹時代的髮梢快意的昂揚起來,我看到風帶來現代的氣息,這氣息讓我的詰問顯得不合時令。我說「中平 保」在當年的日據末期可是你們大濁水社的農業指導員,六十年前族人還是馬偕口裏「風的意志」的族群時,「中平 保」已然在日本的理蕃教育下知悉現代的農業耕種知識,也許你們部落水田的種植就是他傳下來的技術呢?我發出嘆息一般的聲音。我們部落沒有水田啊!年輕人輕快的回答,並且出門請來族老。部落南邊的外太魯閣安穩地蹲坐著,似乎在蓄積下一次歷史的風雲;我看到部落上方的麵包山已經讓礦場開挖成灰白的色澤,山下的部落果然已經不見水田,但見怪石嶙峋。族人或遠赴都城,學習像叢林中的猴子攀爬鷹架,或就近來到收購祖先土地的和平水泥專業區擔任臨時工。離開部落時,我以為我看到蓄積的風雲再度攏罩在外太魯閣山區的上空。
黃昏的澳花村村口,蘇花公路往北的車流果然幻化成一條發光的美麗的蛇身,我只好越過蛇背退向南邊,不願夾雜在往北部趕往都城上班的車流裡。我手中的筆記本記錄著八十六歲族老透露「中平 保」的一絲線索,這條凌亂而不失熱情的字跡彷彿就在迷霧中顯現一條細小而微弱的金陽──「中平 保」有兩個女兒,在今年的二月底自國小退休。
三、跳躍的霧陣
來到蘭陽溪上游的Banun部落(瑪崙部落)已經是旅程的第四天了,我手上的資料驅動著旅次,通常我已經見不到資料上的歷史之人,但我依然能夠從廢棄的部落、新建的社區、泛黃的照片、或者是他們的子孫身上嗅聞到時代的氣息,那氣息徘徊遊蕩在我的歷史之旅上,也跌蕩在我追索的心跳上。我還在想著「中平 保有個女兒」這個微弱的金陽。事實上,「中平 保」的女兒已經是近乎老婦的六十歲之齡了,我追索它的路徑從大濁水社開始,電話裡的訊息一路翻過幾座山來到員山鄉她兒子家,去電時兒子說又已回老家南澳,在南澳,得知「中平 保的女兒」在山上工作,我只好面對錯落在南澳鄉野矗立的山脈中尋找一位老婦的身影而悵然若失。我突然想到,也許在我穿梭大南澳地區的時候,我們確曾擦身而過,只是無法知悉彼此的面目罷了!也許我們曾經想要知悉的事物就在四周一如無聲息的薄霧散去,它們確曾存在,只是無緣遇見,即便是有緣遇見,可能又無緣辨識。整個旅程,似乎是有緣與無緣的追逐!
旅途中,我資料中的人物一如「中平 保」隱現空中,它們有時出現在資料上的部落,有時隨著時空的變異跳躍到另一個部落棲息,更大部份,他們果然成為一坏黃土安安靜靜地眷顧他的子民,我只能找到他們的後代傳述父親的事蹟。他們像是一團團霧氣,將歷史的空間織成千層霧,我想要進入其中,卻往往為霧陣所迷惑。正如每一個不起眼的部落,在當代也織出美麗故事般的迷霧,而我只是一位進入霧中記錄故事的平凡旅人。 Banun部落的報導人在細雨紛揚的室內為我講述先生的事蹟,報導人的兒子趕到部落山凹下尋找工作中的妻子,他說一定要叫妻子回來煮中餐。採訪完,遠望山凹下,有人將一顆顆肥美的蘿蔔棄擲山溝,幾個人影勤勞的移動手腳,報導人的兒子正向那群人中走去,山腰的霧網不一會兒就將蘿蔔田吞噬殆盡,直到我看不清人影,只剩無邊無際的白茫茫的霧向我突然襲來。
四、歸程
蘭陽溪上源一直延伸到思源埡口下的南山部落。昔時,這是一條族人從白狗大山,經梨山、環山,步下思源埡口走出叢林的高速公路,南山部落正好是一座中繼站,族人因為在此炊飯而食,取了「Peyanan」的地名。我的歸程通常也喜歡取山路而回,喜歡沿著百年前的路徑前進,青山綠水總是激起我的思慕之情,儘管南山此處經年瀰漫著濃厚的霧氣,現在就是炊飯而起也是一件不易的事吧,至少炊煙將混在白霧之中。
車行南山,我的旅程一如山路在霧裡盤旋而上。我喜歡撥開謎面般的旅行,每一個迷的解開將又是另一個謎面的產生,它們引領我走向巨大的迷霧之中,又從迷霧中牽引更多的霧點。
思源埡口就只剩幾分鐘的路程,灰白色澤的雪鐵龍在迷霧中奔向充滿鹿角的美地,我知道那是陽光眷顧的部落,再遠一點,就回到了生養我的埋伏坪部落,在那裡,我將蓄積下一個迷霧之旅所將攜帶的養分,因為我知道,歷史上無數個「中平 保」還在等待著我。
原載於1999年2月24日《中央日報》
收錄《迷霧之旅》,頁121-129。
瓦歷斯‧諾幹授權使用